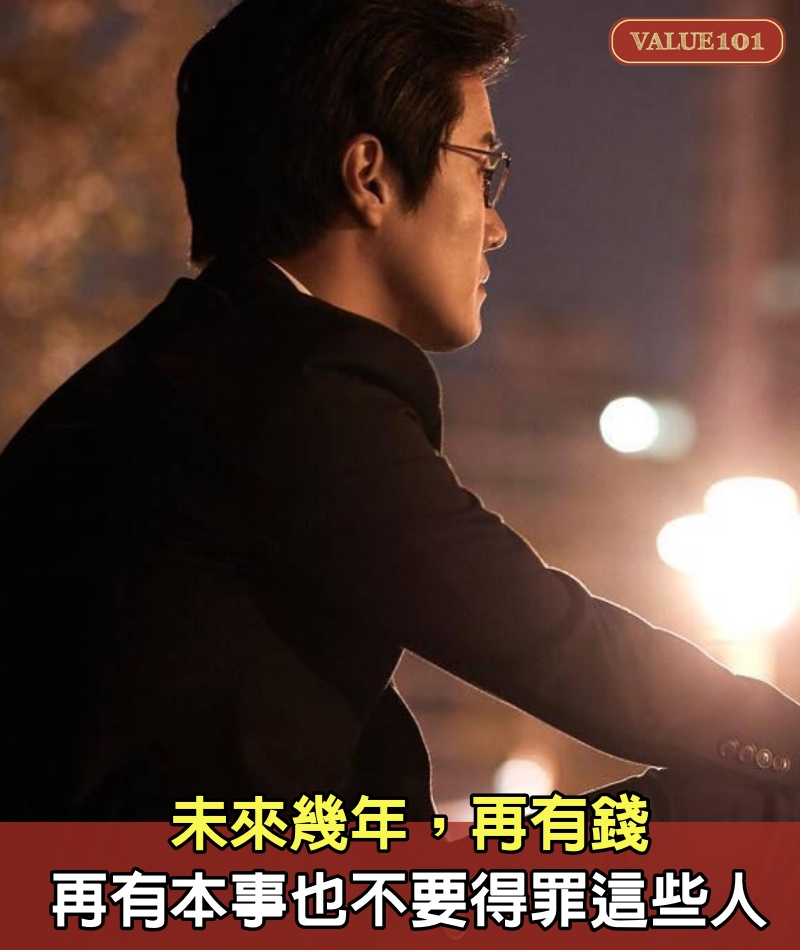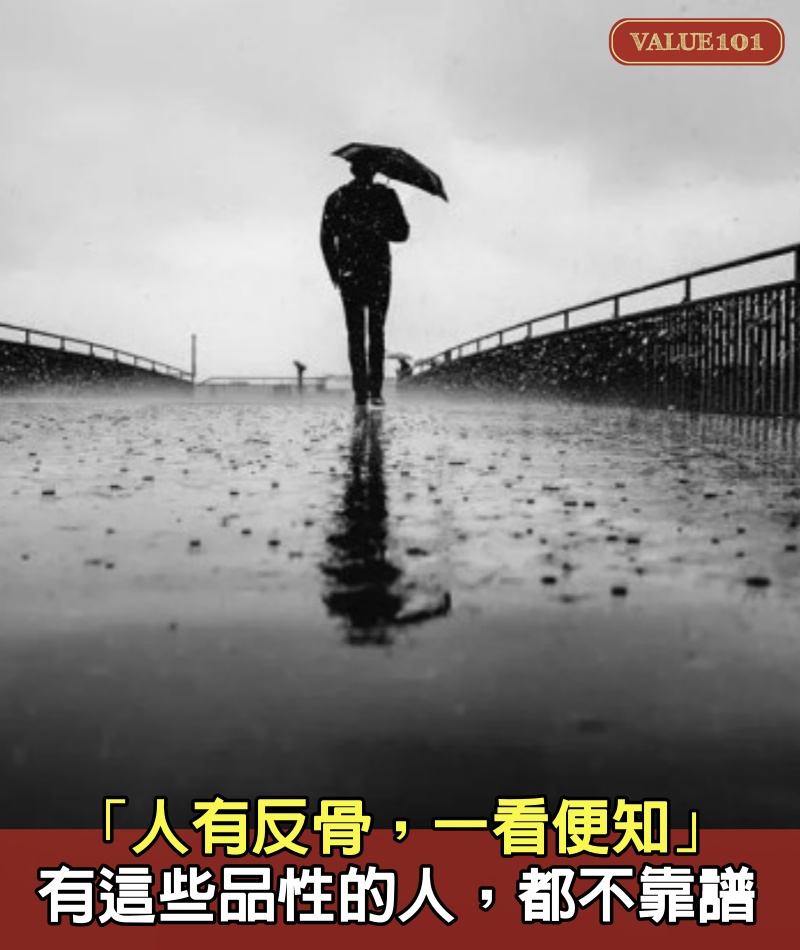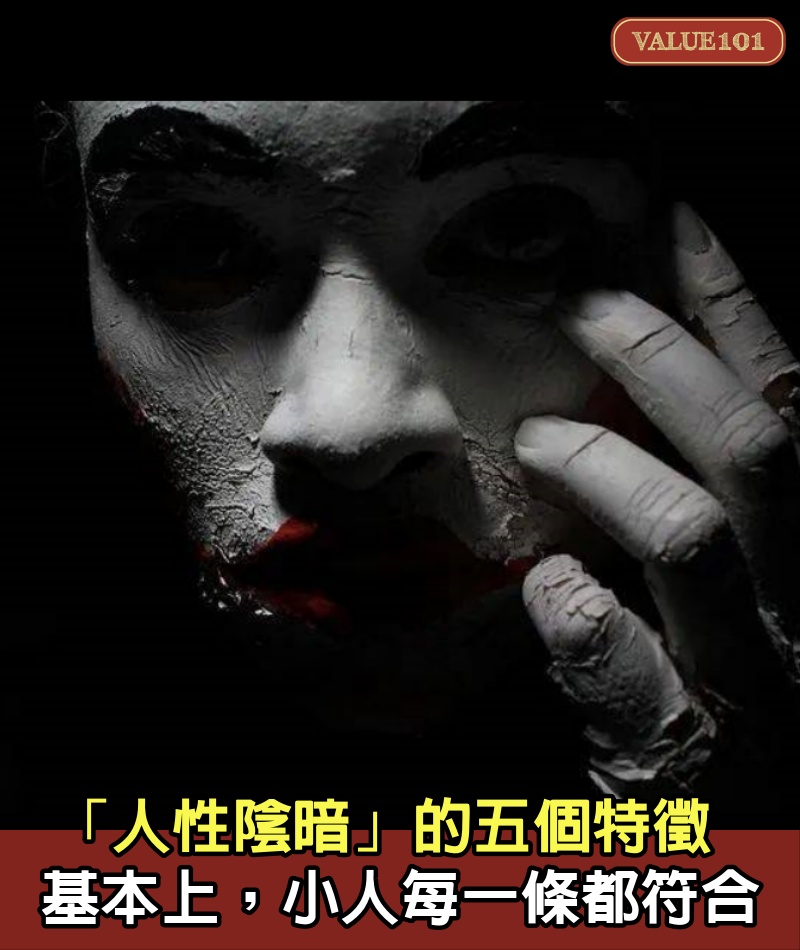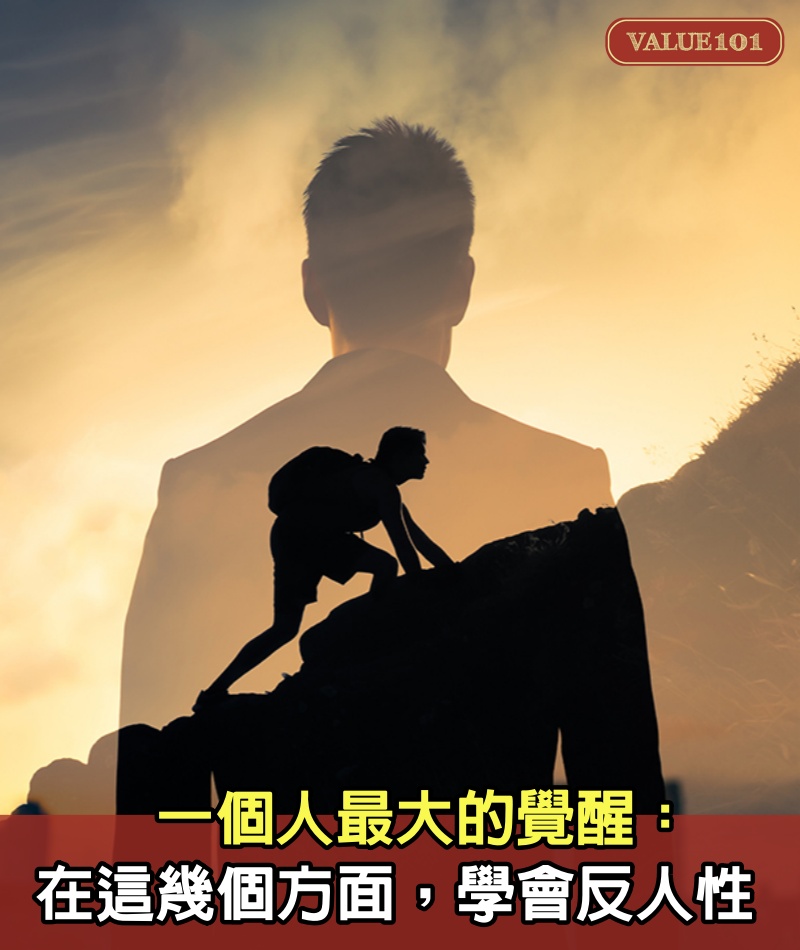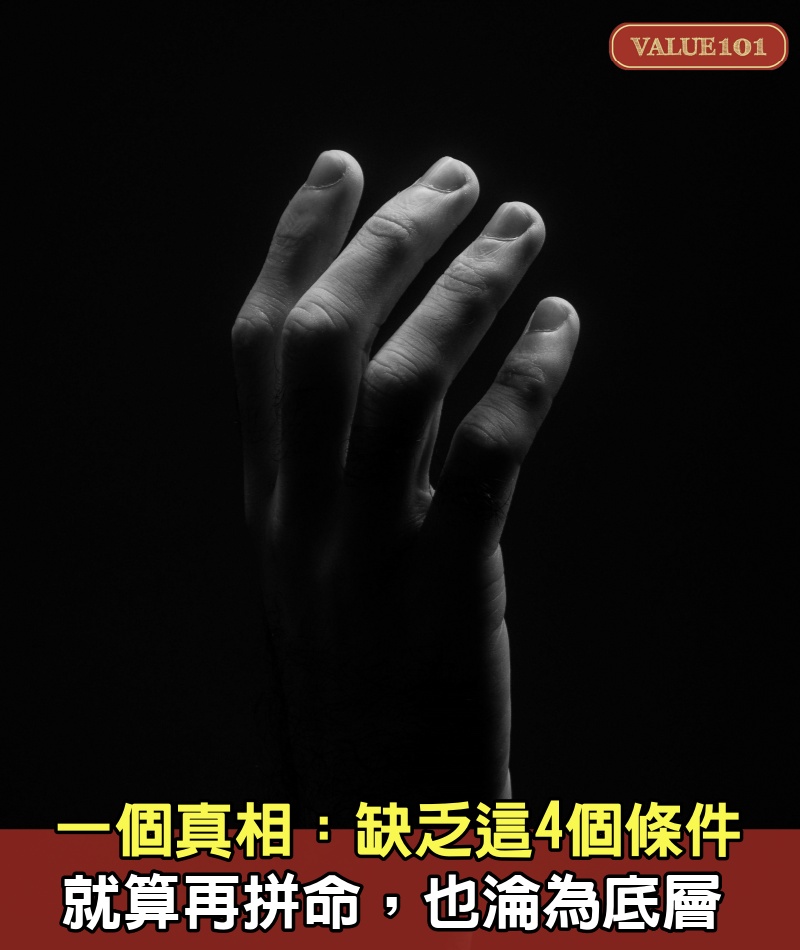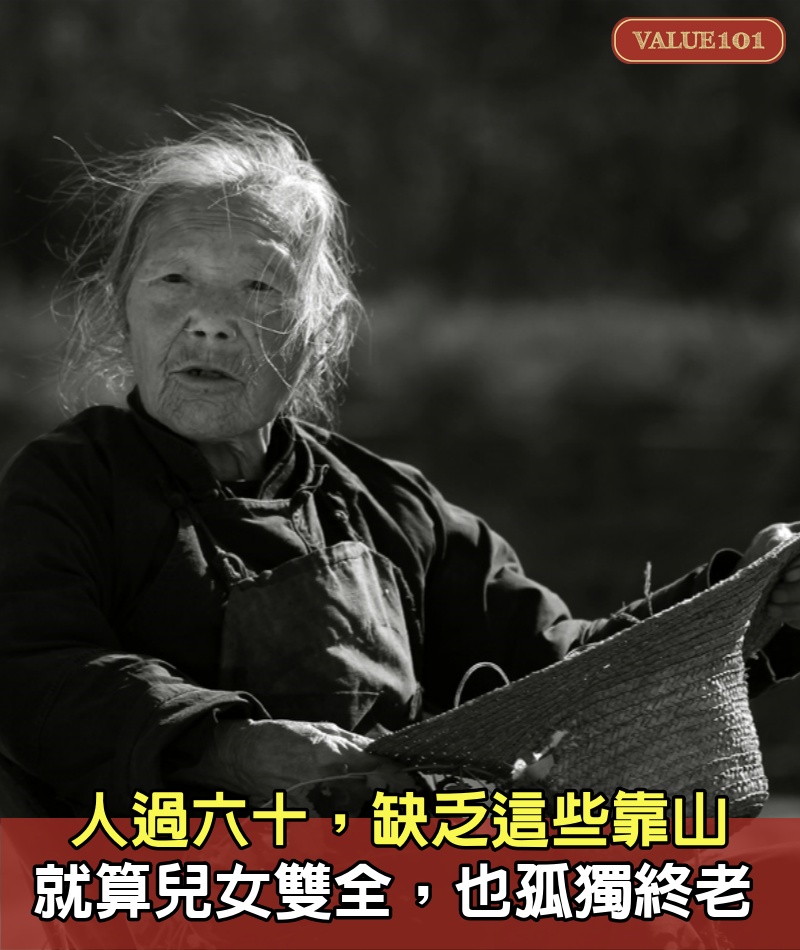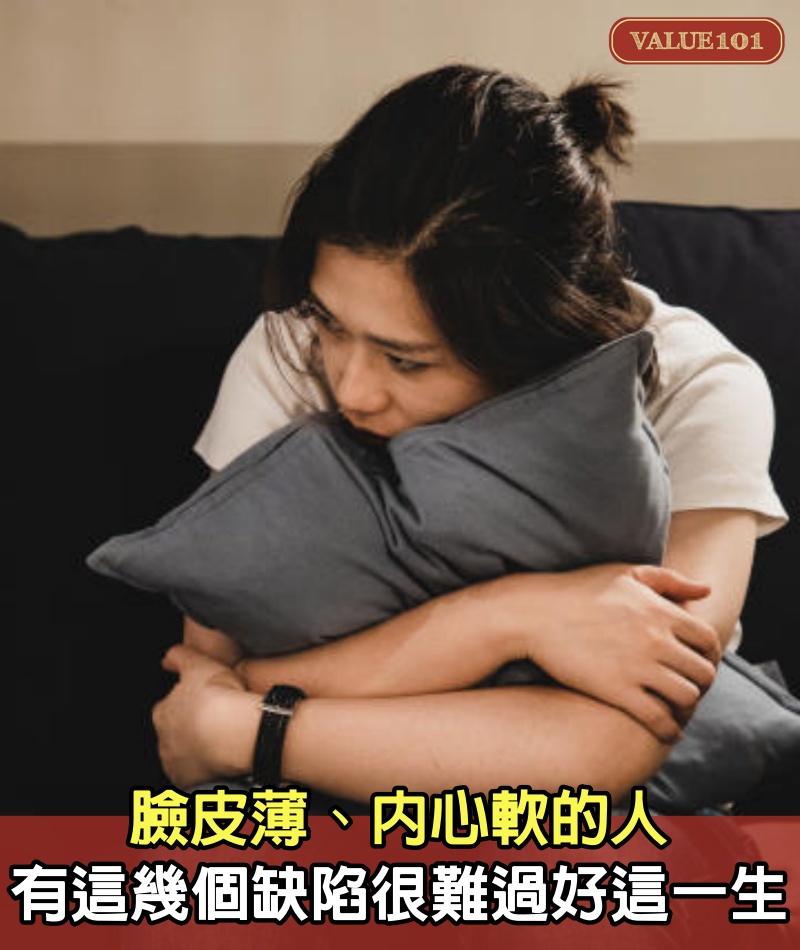認清這1個真相,你才能真正變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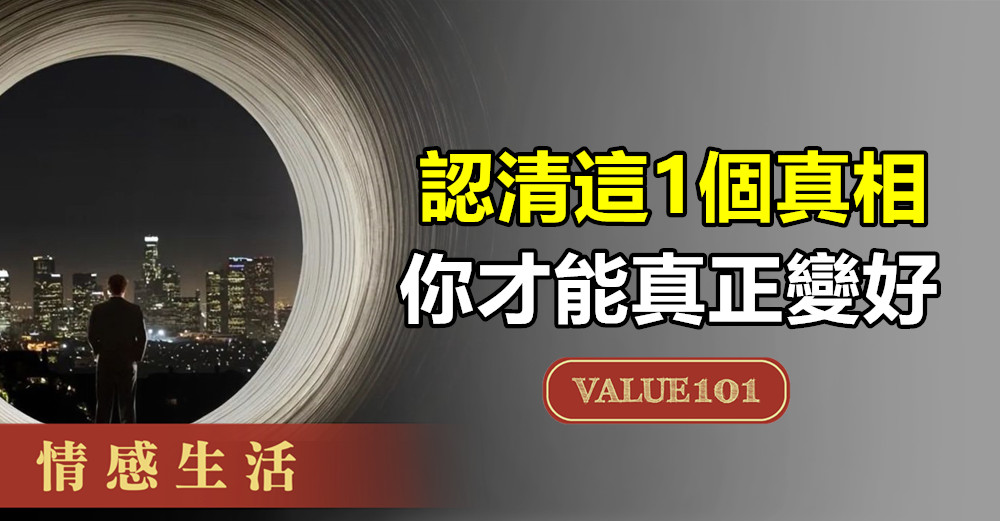
想像一下,你和兩個朋友約好見面。住的更遠的你,為了準時赴約,午飯也沒吃,就早早出發了。
沒想到,到了約定地點,你等了半小時,另外兩個朋友才來。
一問,倆人已經吃過飯了,此刻的你,又餓又生氣,你會怎麼做?
是假裝無事發生,還是如實表達心情?更深層的問題是:
你在自己的感受和照顧別人之間,如何選擇?
01 害怕被討厭,不敢活出自己
前兩天,朋友春雪加班到晚上9點,叫了車回家。上車沒多久,司機就熱情搭訕:“小姑娘,這個點兒才下班啊?”
“嗯,是啊”春雪回答道。
“現在的年輕人,真不容易啊!”
“嗯,是挺累的”
“哎,現在錢真的不好掙啊,你是不知道,我早上今天碰見一個客人,絕了,給我打了個差評…”
春雪有點尷尬,本來累了一天,想听聽音樂,放鬆放鬆,但又不敢不接話,只能順著司機的話說:
“為什麼啊”
司機說:“他坐上車,就開始催,我總不能闖紅燈吧,但他還是一個勁兒的催,最後他上班遲到了,就為這,給我一個差評…”
此刻,春雪有點無奈,花了錢,還要聽對方抱怨,表面上,卻不敢讓話掉地上,應和道:“嗯,是挺過分的”。
“是啊,這人不會早點出門嗎,催我有什麼用?這還不是最噁心的,你是沒見,我那天…”
司機打開了話匣子,春雪只能忍著不適,“嗯嗯,哦哦”的陪了一路。
明明很煩,卻不得不勉強作陪。
這樣的場景,生活中有很多:
逛街時,明明你只是想試穿一件毛衣,卻被導購圍著不放:
“這衣服太襯你膚色了”
“你這麼白,穿我們家另一款大衣,肯定好看,我拿來給你試試”
你明明想逃跑,表面上,卻在尷尬假笑,無奈地接過對方遞過來的大衣。
類似的場景還有:
你一個人坐火車,拿行李,找座位,折騰半天,好不容易入座。一個女生拍拍你肩膀:“你好,可以和我換個位置嗎,我朋友在旁邊。”
這時,坐在你旁邊的女生投來懇切的目光。正當你猶豫時,對面座位上的男生開口了“你就和她換下嘛,我們都一起的”
本想拒絕的你,話到嘴邊,又憋回去了,還是忍著疲累的身體,換了座位。
為什麼,在自己的需求和別人的需求之間,你容易犧牲自己?
因為,只顧自己是會被討厭的。
明明很煩出租車司機,卻不敢表達,因為怕一表達,就會被討厭。
明明很煩導購,卻不敢拒絕,因為怕一拒絕,會被嫌棄。
明明不想動彈,卻被迫換座,因為怕不換座,會被旁邊的人討厭一路。
這一種很正常的情緒。但這種情緒,卻會讓你活的唯唯諾諾,低眉順眼,而你真實的生命能量,被嚴重壓抑了。
02 問題的核心在“小我”
為什麼,我們都在竭力避免被討厭?
因為,被討厭,會有後果。
朋友小A,唸書時,曾被一個女生討厭。走在路上,她主動打招呼,對方直接忽視。來她的宿舍分家鄉特產,她所有的室友都有,唯獨略過了她。
更過分的是,有一陣子,她開始拉攏小A的閨蜜,試圖排擠小A。提起那段經歷,小A又憤怒又痛苦。
被人討厭,確實會讓人很難受。知乎上,有一個提問:“被人討厭是怎樣的體驗?”
有人回答:
“是一種生不如死的感覺”
“心像被釘子扎了一樣難受”
為什麼我們會這麼痛苦?
在阿德勒的《被討厭的勇氣》一書中,有這麼一段:
哲人問:“被別人討厭時,你會有什麼感覺呢?”
青年回答:“那當然是很痛苦啊,會非常自責並耿耿於懷地冥思苦想:為什麼會招人討厭、自己的言行哪裡不對、以後該如何改進待人接物的方式等。”
發現沒,當我們被討厭時,第一反應往往是:“會不會是我哪裡錯了?”之後,這個問題又會上升到:“會不會是我不好”。
我一個發小,經常和我吐槽同事。
“我那天看她加班,好心幫她做了幾張PPT”
“可她倒好,事情沒做好,甩鍋到我頭上...”
“我平時對她多好呀,我媽給我寄的特產,都給她帶一份,她呢,不幫我也就算了,居然還甩鍋給我”
每次吐槽,她會反復強調,自己的“清白”,放大對方的“錯誤”。我能明顯感到,她在向我證明:“她是對的,對方是錯的。”
似乎只有證明了這一點,我才能接納她。而我很想告訴她:“即便你錯了,我也會接納你”
錯誤,是人的一部分,但不是人本身,即使你錯了,並不等於,你就是不好的。
這裡的“對錯”,是思維範疇的,而“你”則是一種存在。“思維”不是你,但很多人會把思維與人畫等號。
這就像拿葡萄藤上的一根枝蔓,來定義整個葡萄藤。心理作家Eckhart Tolle把這個叫做“小我”。
Eckhart Tolle表示,“小我”不是真正的自我,真正的我是一種深刻的臨在,是一個內在觀察的,無評判的心靈之眼。
也就是說,我們的思維不是我們本身,而那個觀察思維的存在才是我們本身。
當我們陷入“小我”時,就遠離了真正的我:
“小我”說:“他討厭你,一定是你哪裡不對,你不夠好......”
當你相信“小我”的聲音時,你會發現,他人的否定,否定了你的存在。於是,你只能唯唯諾諾,不去得罪別人。
而真正的你,嚴重被壓抑了。
相反地,當你意識到,思維不是你。就算他人討厭你,就算你錯了,也無法否定你的存在,你就能擁有被討厭的勇氣,真正的活出自己。
03 害怕背後是“異類思維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