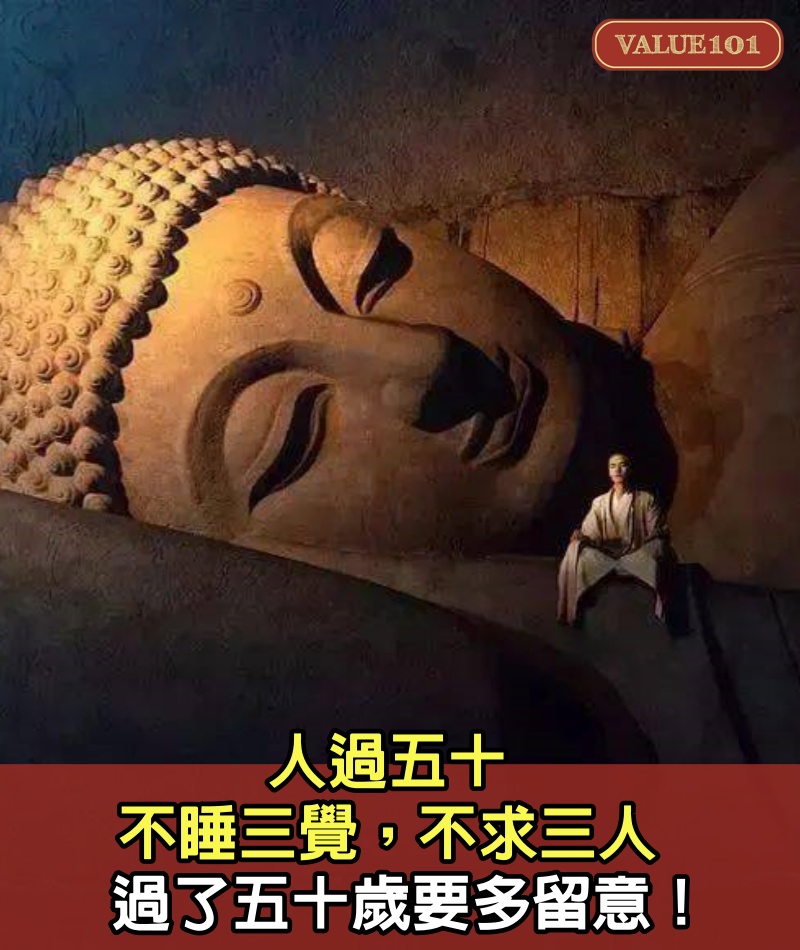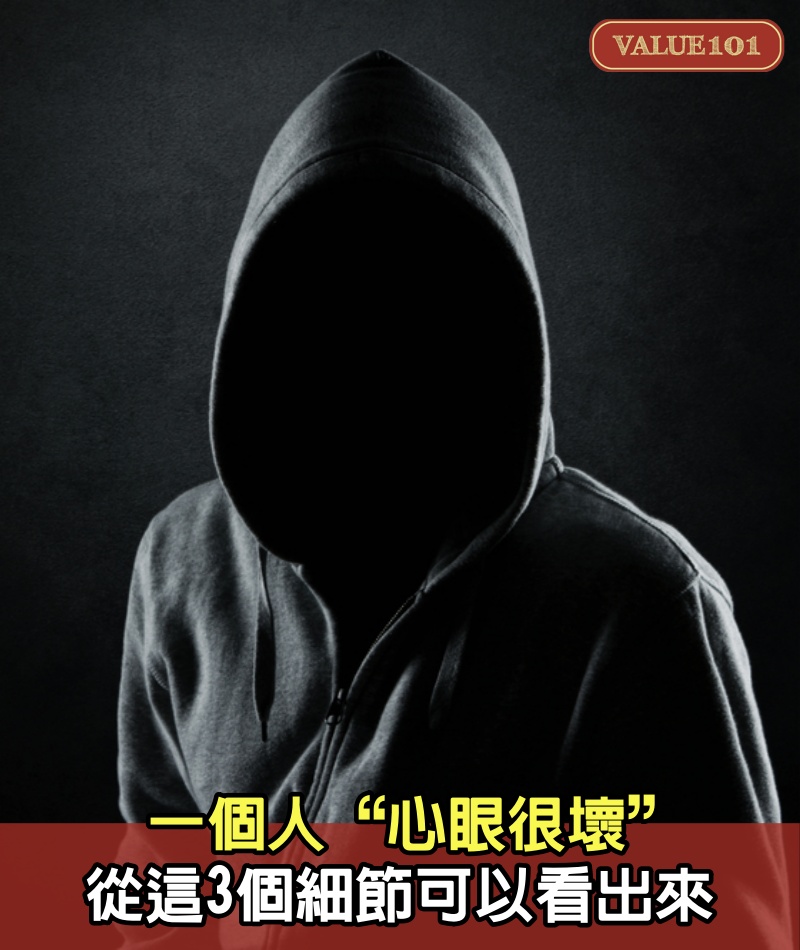柳宗元:人到中年,學會放下

在得知我貶到永州時,我母親比我還要看得開,她怕我去那里孤苦伶仃,執意要跟我來永州。
我內心愧疚,老人家已近暮年,還要跟著我流浪。她似乎看出我的憂慮,安慰我說:
真正聰明的人,是不會為這些往事憂愁的,兒啊,我并沒有因你被貶謫辭退感到難過。
初來永州,我們只能住在寺廟里。寺廟大堂野鳥亂飛,野草茂盛。白天,香客嘈雜,香火煙熏,晚上老鼠亂竄。
有天晚上,一陣風吹來,香火的火苗黏上了布幔,房子陷入火海。我在墻上開了個大洞,抱著母親赤腳沖出去。背后,是一根根帶著烈火的梁柱,狠狠砸在地上,濺起火花。
住處環境差,水土不服,加之缺醫少藥。
來永州不到半年,母親就撇下我,離我而去了。

少年喪父,中年喪母。
我真正成了孤家寡人,孑然一身活在這人間。
我萬念俱灰,悲傷與失意如煙霧般籠罩我,心態的崩潰使身體加速衰老。走路時膝蓋打顫,讀書時健忘,坐下時渾身疼痛,三十多歲的人身體已像五十多歲一樣。
人生,其實就是個不斷失去的過程。
上天帶走了屬于我的一切,不能再讓它帶走我。余生不易,我必須坦然面對,放下悲傷,繼續前行。
于是,我常攜著一壺酒,上高山入深林,一遇好山水,就倒盡壺中酒,一醉方休,醉在這山水中。
山水無意,人有情,我為它們寫下《永州八記》,還替它們改名字,把河溪叫愚溪,山丘叫愚丘,泉水叫愚泉,還有愚池、愚島、愚堂、愚亭...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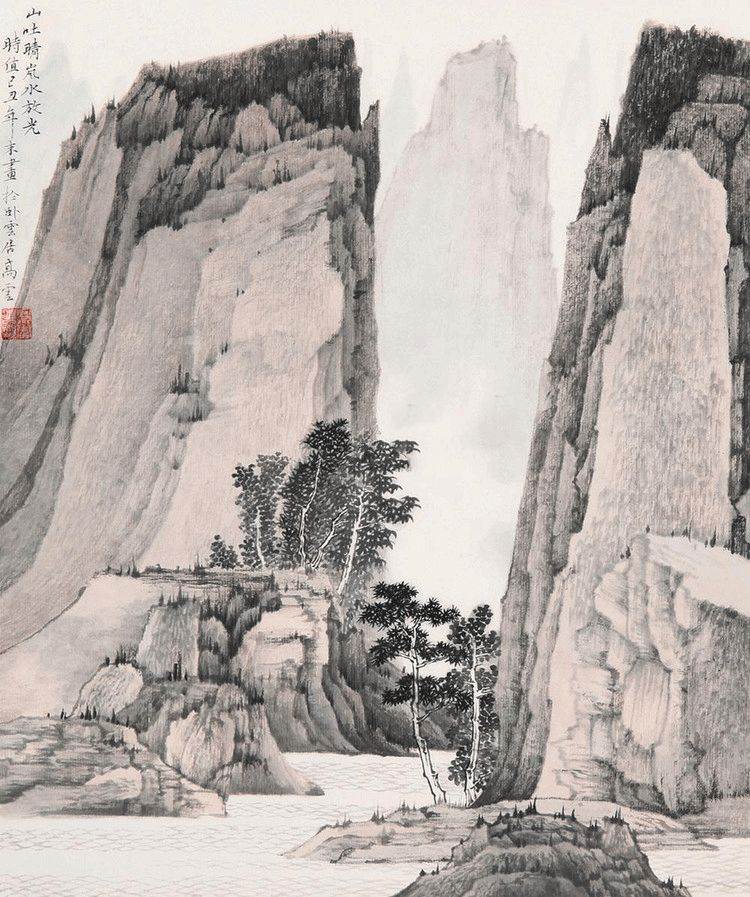
我想:「要不是因為我愚鈍不合時宜,也不會有此遭遇,更不會與你們相遇,不如改個名字,大家一起愚。」
竹石清泉帶走親人離去的傷懷,爬山涉水強健我羸弱的身軀。我心靈逐漸重歸寧靜。
有人說:「中年人有一種無言的傷痛。目送生命的逝去,目送生命的遠行,卻只能目送,無法挽留。」
人一生終會面臨目送的傷痛,只有放下傷痛,保持平靜,才是一種更強大的自救,也才能走得更遠。

4
中年困境四:朋友越來越多,知己越來越少。
自我被貶謫的那天起,昔日酒肉之友、官場之交,都因利益相關,翻臉不認人,甚至說我壞話,以得到我的敵人認可。
而在我遭受親人離去,無依無靠,感到被世界拋棄時,劉禹錫一直沒有拋棄我。
他常寫詩勉勵我,他說:
老柳,不要在寂寥的秋天傷悲了,晴空萬里,鳥鶴凌云時,不如就趁著詩興,寫首詩吧。
十年后,我們終于被赦,回來長安兩個月,劉禹錫就寫了首詩: 玄都觀里桃千樹,盡是劉郎去后栽。
言外之意是朝上那些新人,都是我走了后才提拔的吧?我走了你們都發達了吧?

這次,我們又被派到更遠的地方當官了。我被貶柳州,劉禹錫最慘,被貶猿狖所居,人跡罕至的播州(遵義)。
他母親已八十幾,難以承受遙遠路途的顛簸,但如若不跟劉禹錫一起,就要與兒子生別離。
我想起了自己的母親,流著淚上奏說:
愿以柳易播,雖重得罪,ㄙˇ不恨。
我寧愿自己去更偏遠的播州,只求能給個機會,讓劉禹錫去好一點的柳州吧。也許是上奏起了效果,劉禹錫最終去了連州。
一個人落難時,是最能看出朋友的氣節和真情。
分別那天,我對劉禹錫說:「老劉,二十年來,我們做什麼都是一起。一起改革,一起被貶,一起回京,又一起被貶,如果將來能退休,晚年就當鄰居,種種田,喝喝酒吧。」
只可惜,這個愿望沒能實現,這一別就成了永別。

47歲那年,我在柳州生了場大病,自知大限已至,披衣點燈,寫下絕筆信:
......我不幸,卒以謫ㄙˇ,以遺草累故人。
我希望劉禹錫能幫我把文稿都整理出版,把我的兒女撫養成人。
那是我對這個世界最后的期待。
記得一句話這樣說:「人沒有朋友是最純粹最可憐的孤獨。」
其實中年不可怕,可怕的是你孤軍奮戰。
人活到一定年紀,朋友會越來越多,交心的會越來越少。放下無謂的社交,交二三知己足以。

我是個天生孤獨患者,我不像劉禹錫,樂觀豪放,笑對人生苦難;
也不像白居易,一路被貶,也能瀟灑不羈。
我只能一路放下,才能繼續前行。
中年過后,不斷在失去,也不斷在得到。
失去的時間越來越多,你的閱歷也越來越多;
剩下的人生越來越短,走過的路卻越來越長;
放下,恰恰也是擁有的開始。
因為你緊握雙手時,里面什麼都沒有;而你打開雙手時,世界就在你手中。